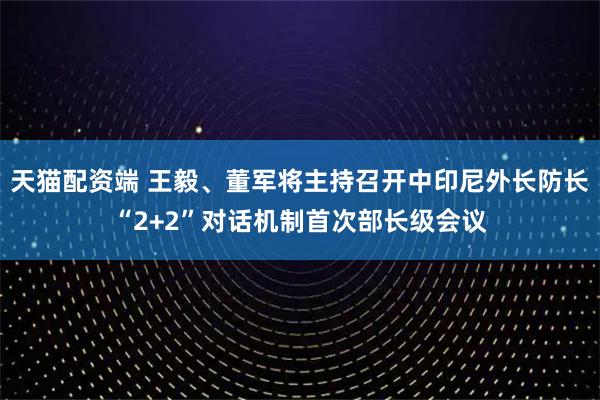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转载请后台留言,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全文共7921字 | 阅读需17分钟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玖期
785年正月,在位五年有余的唐德宗改元贞元,为了营造新元气象,德宗特下诏令大赦天下,而已被贬谪新州一年有余的卢杞也因此调任吉州长史。面对突如其来的转机,卢杞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又开始摆出昔日在朝堂上那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甚至在贬所就扬言“吾必再入用”。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此次遇赦不过是他仕途上的回光返照。
唐德宗对这个昔日的“仆臣”很是眷顾,没过多久,又打算提升卢杞为饶州刺史,这下招来了大多数朝臣的反对。先是给事中袁高上书声言卢杞“幸免诛戮,唯示贬黜,寻已稍迁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 …… ”,谏官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也纷纷上书,“极言杞罪四海共弃,今复用之,忠臣寒膺,良士痛骨,必且阶祸”,而后宰相李勉和散骑常侍李泌的进言则彻底断绝了卢杞的回京之路,唐德宗终于改变了主意,诏令卢杞改任澧州别驾,最终“杞寻卒于澧州”。

卢杞像
读到这里有人不禁会问,卢杞到底为人如何?竟招致朝廷上下的一致抵触。若读完他的生平事迹,大家会发现,其最终贬死异乡实属多行不义必自毙。
卢杞出身范阳卢氏,其祖父卢怀慎本是唐玄宗时的宰相,卢怀慎一生廉洁谨慎,注重以俭治家,被世人称颂。其父卢奕承继家风,谨愿寡欲,刚毅朴忠,天宝十四载(755),安史叛军进犯东都洛阳,城中人吏奔散,卢奕却坚持留守府台,最终为叛军所害。卢氏祖上多出清节忠烈之士,按说受这样的家风影响,卢氏子弟当多为轻利好义、矢志忠诚之人,可卢杞却偏偏未受如此优良门风的半点熏陶,其一生所为与父祖的处世之道大相径庭。
卢氏一门始终以勤俭持家,加上父亲卢奕的英年早逝,使得卢杞早年家境贫寒,一家人只能租住在洛阳的废宅中勉强度日,但卢杞却不甘生活清苦,更不愿寒窗苦读,而是凭着自己的口舌之能与一班市井之徒打得火热。与他同乡的一位叫冯盛的书生整日发奋读书,很少参与街谈巷议。卢杞很看不起他,认为他是不谙世事的书呆子,于是在碰面之时故意羞辱他,指着冯盛只装着墨的口袋笑他穷酸,冯盛严肃地对卢杞说道:“天峰煤和针鱼脑,入金溪子手中,录《离骚》古本,比公日提绫文刺三百,为名利奴,顾当孰胜?”于是搜卢杞的口袋,果然发现有名刺(即名帖、名片)两三百张。卢杞却不以为意,继续整日与他那些狐朋狗友鬼混,招摇于闹市之间。
因为卢家祖上的功劳,卢杞得以门荫入仕,出任清道率府兵曹,后又入京历任鸿胪寺丞、殿中侍御史、膳部员外郎。卢杞因为生得面目丑陋,招来了许多同僚的私下讥讽,但因为卢氏一门的威望,加上卢杞平时对衣食穿着不甚在意,世人都以为他继承了卢怀慎的清节,对他的品性却不甚了解。卢杞却把这些记在心里,并暗中观察朝廷的局势,为自己的仕途谋划。当时的唐王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已是一片风雨飘摇。藩镇、宦官、权臣等势力在朝廷内部盘根错节,相互争斗,卢杞凭借自己的口辩之能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媚权谄贵,竟能左右逢源,步步升迁,但他善于钻营的品行却深为有识之士鄙夷。后来卢杞出任忠州刺史,因其地属荆南镇管辖,于是在上任之初,卢杞非常殷勤地前去拜访顶头上司、荆南节度使卫伯玉。卫伯玉乃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时之名将,向以持重干练闻名于世,对卢杞的谄媚钻营十分鄙视,见他登门造访,卫伯玉十分冷淡,寥寥数语便把卢杞打发出门。卢杞很诧异,真没想到自己这一身纵横官场的逢迎本事对这位老帅丝毫不起作用,眼见不受顶头上司待见,卢杞心里明白自己在这里很难有立足之地,于是便托病请辞,返回京城历任刑部员外郎,金部、吏部郎中等职,之后又离京出任虢州刺史。虢州地处关中与河南交界本财配资,属唐王朝的统治核心区域,交通便利,信息畅通,卢杞在这 里韬光养晦,经常与朝中一些官员互通有无,以借此谋求仕进。很快,机会便来了。

“土皇帝”权力的象征——唐鎏金狮钮“契丹节度使印”
大历十四年(779),唐代宗李豫驾崩于大明宫紫宸内殿,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德宗少年时经历了安史之乱,做太子后又目睹了藩镇割据、宦官干政的乱局,对大唐中衰深感痛心,所以在即位之初,以强明自任,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打击藩镇势力,很想有一番作为,但他处事过于操切,缺乏识人之明,用人之长却不能抑其之短,施政缺乏长远的眼光,致使朝局愈发动荡。

唐德宗李适像
德宗起初任用老臣崔祐甫为相。崔祐甫为人忠贞正直,执政宽简,坚持唯才是用,使得自天宝以来混乱的朝局有了转好的趋势,但崔祐甫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上任数月便身体抱恙,于是便举荐杨炎代自己为相。杨炎素有文才,德宗也是久慕其名,于是欣然召杨炎回京,任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让其主理朝政。杨炎不负皇命,上任伊始便着手解决边疆战事吃紧、朝廷财政困难等问题。特别是针对当时均田制被破坏,租庸调制废弛的情况,杨炎提出以“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以“计资而税”代替“计丁而税”,改征收实物为征收货币,合并徭役名目,集中纳税期限,从而大大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中国古代税收思想家·杨炎》印花税票
杨炎以其非凡的理政之才为化解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出现的种种统治危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获得了唐德宗的信任,但杨炎这个人心胸狭隘,一朝得势便开始排斥异己,任用私人。杨炎早年曾投于前任宰相元载的门下,并受到他的提携,后来元载获罪被赐死,杨炎也受到牵连而被贬官,而主持审理元载一案的是左仆射刘晏,杨炎因此怀恨在心。等到他回朝掌权后,便挖空心思想要扳倒刘晏,于是向德宗诬告刘晏想要谋反。德宗不辨真伪,竟然命人将刘晏处死。这件事在朝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很多人为刘晏鸣冤,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多次上表朝廷,询问刘晏何罪被杀,并表达了对朝廷的不满。眼见刘晏之死影响如此之广,杨炎也备感压力,竟然派使者到各藩镇说处死刘晏是德宗的本意。这件事后来被德宗得知,致使李适对杨炎顿起杀心,由于顾忌他在朝中的声望,只好暂时隐忍,但从此对杨炎不再信任。眼见朝局又因党争而愈发混乱,德宗认为应拔擢一批外臣入朝,以打压杨炎等位高权重之人的势力。恰在这时,一份奏疏引起了德宗的注意。
时任虢州刺史的卢杞上奏,称虢州当地有三千多头官猪,因为这些猪数量较多,严重影响了当地百姓的生活。饱受藩镇割据、朝廷党争困扰的唐德宗看到这封奏疏后,不禁觉得有些新奇,心想当下还有如此关注民生的州官,他看了下落款,上面写着“臣虢州刺史卢杞上奏”。德宗对“卢杞”这个名字还是有些印象的,知道他是忠烈之后,还颇有辩才,于是一时兴起便批复将这些猪移往同州。但德宗不知道的是,卢杞上这道奏疏有着自己的小算盘,他当然知道宰相杨炎的专权已经引起了德宗的反感,便有意上这道奏疏以示自己勤于政事,不介入党争。在接到德宗的批复后,卢杞心中暗喜,于是再上一道奏疏声称同州之民也是陛下您的子民,如果将这些猪移往同州,同样会成为当地的祸害,不如将这些猪分给贫苦的百姓,以示天子仁德。德宗接到卢杞的回奏,对他很赞许:“世间难道真的有如此忠于职守的干臣吗?”高兴之余,连连称赞卢杞有宰相之才,最终大笔一挥,诏令卢杞入京任御史中丞。
德宗的做法未免过于操切了,而让他更没想到的是,这个未经深思熟虑的决定竟然差点将刚刚走出战乱的唐王朝推向另一个深渊。卢杞回京就任后,马上又开始到处疏通关系,联络同僚,其间少不了要拜访一下朝中的几位大佬,这其中就包括“尚父”郭子仪。这位曾经为大唐中兴立下过赫赫战功的老将在听到卢杞来访后,竟然慌忙披衣而起,屏去侍妾,亲自到门外迎接,在与卢杞交谈时也是面带赔笑。等卢杞走后,侍从们搀着郭子仪回房,发现他仍面带惊恐之色,额头上出了很多冷汗。家人们不知郭子仪为何会作如此神态,便向他询问缘故。郭子仪擦了擦汗,说道:“卢杞相貌丑陋而又心底阴险,左右的人见到他必定会耻笑,如果这样,待他来日掌权之时,我们家族必定会为其所害。”郭子仪对卢杞的为人看得很透彻,果不其然,在卢杞回京之后不久,朝廷内部便又刮起了政治风暴。
因为陷害刘晏一事,唐德宗对宰相杨炎的信任大减,为了对其加以制衡,德宗提任卢杞为御史大夫,之后又任命其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任杨炎为中书侍郎,由二人同时秉政。杨炎很看不起卢杞,因为他相貌丑陋,又无文才,所以经常托病不与其共事。卢杞见杨炎对自己如此怠慢,便怀恨在心,挖空心思地想要扳倒他。正赶上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叛,德宗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军平叛,杨炎劝谏德宗说李希烈为人没有信义,如果此次他打败了梁崇义,那以后必会尾大不掉。可是德宗却没有听从杨炎的谏言,执意要李希烈率军前往。但情况正如杨炎所料,李希烈之所以肯出兵平叛,其实是为了扩充实力,占据梁崇义的地盘,所以在半途中,李希烈假称天气不适合作战而突然暂停进军。消息传到朝廷,德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在一旁冷眼观看的卢杞则抓住时机向德宗进谗,说一定是杨炎对李希烈不满,暗中作梗,才导致李希烈停止进兵。德宗不辨真伪,竟听信了卢杞的谗言,心中对杨炎大为恼火,但眼下战事正值千钧一发之时,德宗只好暂且忍耐,派使者持节到军前,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兼汉南北兵马招讨处置使,李希烈才同意继续进兵平叛。经过这件事,唐德宗对杨炎更加不满,而一旁的卢杞心中则暗自高兴,他认为扳倒杨炎的时机到了,于是四处寻访与杨炎有过节的人,最终他选中了严郢。
杨炎当政之时,曾提出在关中一带实行屯田以充军需,而时任京兆尹的严郢却对此提出异议,引得杨炎对他很是不满,但严郢却没有顾及杨炎的想法,反而又对朝廷制定的一些法度提出疑问,最终招致杨炎的嫉恨。他暗中指使御史张著等人上书诬告严郢,导致严郢被罢官。卢杞抓住杨炎与严郢的矛盾,趁德宗让宰相荐才之时,推荐严郢出任御史大夫,而杨炎则举荐崔昭和赵惠伯。德宗此时对杨炎已是非常反感,对他的意见更是听不进去,反而斥责他的见解不够周全,并借机罢了他的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任为左仆射。
杨炎失去了执政的权柄,他心里很清楚,这是卢杞在一旁作祟,于是在上朝谢恩之时,故意避开卢杞,不与他见面。卢杞知道杨炎对自己怀恨在心,于是便指使严郢访查杨炎的罪行,最终查出杨炎曾让时任河南尹的赵惠伯为他出卖洛阳的私宅,而赵惠伯却直接将此宅作为他的官署。严郢审理此案后,认为赵惠伯故意抬高了价格,使得杨炎所获之利超过了宅子的价值,卢杞更是指使有司官员判定杨炎监守自盗,应处以刑罚。因为杨炎所建家庙地处玄宗朝宰相萧嵩家庙的故地,卢杞便趁机构陷杨炎,称当年萧嵩想在此建家庙,可当地却有谶语称此处有王气,因此玄宗才让萧嵩把家庙迁往他处,而杨炎却故意在此建家庙,说明他心怀异志。其实德宗此时对杨炎的忍耐也到了极限,所以在听完卢杞的话后,德宗未加思量就让三司复查此案,最终在建中二年(781)十月十日,唐德宗正式下诏宣布,尚书左仆射杨炎结党营私,败坏法度,但为顾全大局,特加宽宥,贬为崖州司马。崖州地处如今的海南,唐朝时期还属未开化的荒蛮之地,只有朝廷重犯才会被流放至此,杨炎接诏之后心如死灰,真没想到自己会栽在卢杞这个小人手中,但皇帝旨意已下,他此刻已是阶下囚,只能任人摆布。在随行宦官的监押下,杨炎踏上了茫茫的不归路。跋涉数月后,杨炎来到了容州城外的一处险关,此处地势陡峭,有双峰相对,中间小径甚为狭窄。杨炎行至此处,不觉心生恐惧,忙问随行之人此处为何地。押解他的差役告知他此处名为鬼门关,杨炎一听,心中顿生不祥预感,他仰天而叹,随口赋诗道:“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吟罢,杨炎的心中一阵感伤,他知道,自己也许真的到了最后的时刻。

北流天门关石壁,古称鬼门关
杨炎的预感最终不幸应验,德宗果真没打算就此放过他,在行至离崖州仅百里之距的一处荒野,随行的宦官秉承皇帝的旨意,将杨炎勒死。消息传到京城,卢杞长出了一口气,昔日的对手就此退场,自己终于可以独掌朝政了。但以他的品行和才干定无法维持当时岌岌可危的朝局,更无力将风雨飘摇的大唐拉回正轨,而反观昔日的同党严郢却在御史大夫任上颇有卓绩,卢杞看在眼里,心生疑忌:杨炎之死是自己指使严郢一同制造的冤狱,如果其日后受到德宗的拔擢,再把构陷杨炎的责任都推到自己头上,那岂不是大祸临头!想到这里,卢杞内心顿起杀机,他决心要除掉严郢以绝后患。恰逢太尉朱泚、卢龙节度使朱滔兄弟不和,而朱泚的判官蔡廷玉借机离间他们二人,后来事情败露,朱滔奏请要杀掉蔡廷玉,但德宗最终没有同意,只是将蔡廷玉贬官。殿中侍御史郑詹派属吏监送蔡廷玉,可蔡廷玉却在中途投水而死。消息传到朝廷,卢杞趁机向德宗说:“蔡廷玉是朱泚的属下,恐怕他会怀疑蔡廷玉之死是陛下您的缘故,应该即刻命三司审问郑詹,严郢作为郑詹的上司,一定跟这事脱不了干系,也应该一并拿问。”最终在卢杞的暗中操控下,郑詹被杀,严郢被贬为马州刺史,后死于当地。
卢杞终于如愿以偿地除掉了他的政治敌手,但他口蜜腹剑的小人行径也逐渐为同僚尽知,许多人耻于与其为伍,更有诤臣上书德宗,直言应贬斥卢杞,以正朝纲,但德宗被卢杞的巧言令色所蒙蔽,反在其构陷之下,将韦伦、刘暹、萧复等一干正直的大臣贬黜,对卢杞却倍加重用,言听计从。但卢杞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犯了众怒,为了保住权力和地位,他必须抱紧德宗这棵大树,才能避开众人的口诛笔伐,而他讨德宗欢心的手段就是敛财。
当时,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王朝,国内户口减半,经济衰退,已不复往昔盛世景象,据考证,建中元年(780)天下两税钱共计3000余万贯,抛去各地州府留用的2050万贯外,上供朝廷的有950万贯, 再加上盐利600万贯,粮食收入200余万石,当年朝廷总收入共计1700余万贯石,可中唐时期,藩镇林立,各地节度使时有叛乱,致使朝廷每年用于平叛的军费大笔增加,建中三年(782)四月,度支使 杜佑上书德宗,声言朝廷每月的军费开支需要100多万贯钱,而国库的存粮和钱款只够支付数月,只有再额外凑够500万贯,才能勉强应付半年。德宗看到杜佑的奏疏便向卢杞询问情况,卢杞心中一紧,认为杜佑是在拆他的台,故意在德宗面前揭露他当政的过失,于是转而向德宗诬陷杜佑才不堪任,并推荐其同党赵赞取代杜佑。此时卢杞“圣眷正隆”,德宗轻信了卢杞的谗言,把杜佑贬出朝廷。可是国库空虚、难以为继却是当下的实情,怎样才能缓解朝廷财政的压力呢?卢杞可没有杨炎的本事,他能想到的就是去搜刮民财。他先是盯上了长安的富商,经历了代宗、德宗两朝的休养生息,唐王朝终于恢复了些许元气,长安市面上的商贾又渐渐多了起来,而这些都被卢杞看在眼里,他认为要想缓解当下朝廷的财政危机,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套取这些富商巨贾的财富,以此来充盈国库。于是在征得德宗同意后,他指使同党赵赞、韦都宾等人强征长安商贾的财产,凡家产超过万贯的商户,可留万贯钱留作家用,其余的都要被朝廷“借”为军费,等到战事平息之后再偿还。消息一出,民间舆论一片哗然,但卢杞已经顾不了许多,在他的授意下,京兆少尹韦祯、长安尉薛萃等人天天带着官差挨家挨户地搜罗资财,对一些不愿缴纳家产的商户甚至不惜动用刑罚,结果酿成了被征敛者上吊自杀的惨剧。

隋唐含嘉仓刻铭砖
可就算是这样,也不过搜罗了88万余贯的钱财。卢杞又下令将长安城内所有的当铺积存的财物一律借去四分之一,还封闭了那些寄付钱物的柜窖,这样一来导致长安市上所有的商业贸易几近停滞,民生无以为继。走投无路的百姓纷纷涌上街头,拦住了卢杞的车驾,卢杞本来还想施展口辩之才,哄骗一下百姓,可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卢杞见情况不妙,不得不狼狈逃离现场。德宗见向商贾借贷一事影响恶劣,不得不下诏停罢,但军费紧张的问题却未能得到解决。没办法,卢杞及其党羽又转而盯上了长安市民。建中四年(783)六月, 卢杞授意赵赞推行“税间架”和“算除陌”两项税收举措,由于时间仓促,所以仅在京师一带实行。“税间架”类似于如今的房产税,官府规定,“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 而“算除陌”类似于交易税,“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这两项税收都涉及京师百姓的生活。在那个战乱频发的年代,国家动荡,经济萧条,而税负的增加更给这些贫苦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一些权贵、富商却仗着官府的势力,隐瞒自家财产,暗中进行黑市交易,致使官府所收赋税远不及预期,只得加紧盘剥小民百姓,终致群情激愤,民怨沸腾。长安士庶纷纷把矛头指向了卢杞,但为了赢得圣心,卢杞已经顾不了许多,他指使手下巧设名目,变相向长安百姓增加税负,虽然这样搜刮到了部分财富,但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不但损害了国家的经济体制,降低了朝廷的威信,也使卢杞彻底丧失了士庶的支持。
正当朝廷为筹集平叛军费而焦头烂额之际,各地 藩镇的叛乱却愈演愈烈。本来被朝廷授权平叛梁崇义之乱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自恃功高,想要割据梁崇义原有的地盘,可是朝廷却没有允准。李希烈大怒,竟然勾结卢龙节度使朱滔、魏博节度使田悦等人一起叛乱。战火瞬间燃遍中原各处,朝廷派大将李勉、哥舒曜等率军平叛,可叛军气焰正盛,朝廷军队几次与之交战不利。战火迅速蔓延,唐德宗只得召集各地兵马平叛。建中四年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奉诏率本部五千兵马冒雨赶到长安。本来因为国库空虚,这些戍边士兵经常挨饿受冻,饷银也少得可怜,而这次正赶上朝廷召集他们平叛,将士们都想着会获得一些朝廷的犒赏,所以很多人都带了家眷,想要多得到些赏赐。可到了长安才发现,朝廷送来的犒赏只是一些粗茶淡饭。泾原将士愤怒不已,由此发生哗变,乱兵直奔皇宫而来。有百姓发现兵变后,纷纷四散躲避。这些哗变的士兵倒还颇有政治头脑,到这个时候还不忘收拢人心,他们向着混乱的人群喊话说:“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连叛军都知道朝廷推行“税间架”“算除陌”的弊病,可见卢杞等人所为有多不得人心。唐德宗听到泾原军兵变,慌忙派普王李谊和翰林学士姜公辅带着几十车绢帛前去劳军。可是愤怒的士兵已顾不得这些,他们斩断皇城门,直奔大明宫丹凤门外列阵,高呼要面见皇帝。不可思议的是,由于之前叛军声言要替百姓请罢苛捐杂税,长安市民反而对这些哗变的军队产生了好感,在叛军进逼皇宫之时,“小民聚观者以万计”。这些京师的百姓选择了观望,他们不再对叛乱感到恐惧,更没有一人站出来拥护皇帝。唐德宗听到叛军已逼近皇宫的消息,惊得手足无措,慌忙带着卢杞、关播等一众亲随近臣出逃奉天。后来尚书右仆射崔宁也从长安脱身,前往奉天投奔德宗,一路上,尽是山河破碎,满目疮痍。崔宁为之悲泣,对身边的亲随说:“上聪明,从善如转规,但为卢杞所惑至此尔。”可这话后来竟然传到了卢杞耳朵里,使他对崔宁顿生怨恨,便唆使其党羽京兆尹王翃在德宗面前诬告崔宁心向叛军,还伪造了崔宁给叛军的书信,德宗信以为实,盛怒之下,竟下令杀了崔宁。
卢杞的倒行逆施注定了他的下场必是遭万人唾弃,这场叛乱最终被李晟、浑瑊等大将合力平定,德宗终于又回到了长安,可是卢杞却再也没能回到朝堂。原来在平乱过程中,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率军前来,李怀光生性粗疏固执,多次声言卢杞、赵赞等人都是奸臣,自己见到皇帝一定会奏请杀了这些国贼。卢杞听到风声后心里害怕,便向皇帝进言让李怀光乘胜追击叛军,想要把他支走。李怀光率军进驻咸阳,越想越生气,自己亲冒箭矢,率军平叛,皇帝竟然连见都不见自己,他认定这必是卢杞等人向皇帝进谗言,才使得皇帝疏远自己,于是李怀光继续上书数落卢杞的罪行。当时战事紧急,李怀光作为平叛的主将,身有大功,德宗不得不顾及他的意见,最终不得已下诏贬卢杞为新州司马。卢杞的被贬可谓大快人心,但德宗却始终对他念念不忘,于是便有了开篇的一幕。一年之后,德宗改元大赦天下,想要提升卢杞的官职,却遭到了举朝上下的反对,德宗不得不作罢,而卢杞最后的希望也由此断绝,不久便抑郁成疾,客死异乡。
文章作者 文史作家 李大鹏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嘉创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